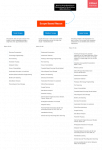诗歌赤子樊忠慰
陈晓兰(以下简称陈):樊忠慰,欢迎你做客《文学话坛》,自你的诗集《绿太阳》出版以来,你受到了文坛的关注。先是《绿太阳》获省政府文学奖,2004年又被授予王中文化将,面对这些荣誉,你有何感想?

樊忠慰(以下简称樊):的确如此,《绿太阳》出版后,获得了云南省政府文学奖,云南民间王中文化奖,得奖是好事,但不是目的。感谢出版社和评委对我的认可和褒扬。得奖可以表面化地提升诗歌的品质,不管评奖有多公正,一切艺术的试金石是时间,而不是获奖。对于我,写作是为了指向终极,叩问彼岸,淡化病苦,揭示、演绎和表现人生的价值,尊严,苦难与美好。在幻听的炼狱,给自己虚构一个天堂,从1991年8月开始,我就有不少诗作在省内外报刊发表,特别是北京的《诗刊》、《十月》,云南的《滇池》、《边疆文学》都多次集中发表我的诗作,对我鼓励很大,在此一并致谢。荣誉有时是一种虚妄的东西,圣洁、空洞而无聊。获奖后,一些媒体夸大而歪曲的炒作,不仅令我无奈和难堪,更让我这个热爱诗歌的人,也不得不从负面审视语言的能量。我是一个信念坚定,意志超常的人,或者说是一个有灵魂的人,不然,这么多年的疾病我恐怕挺不过来。怎么编排我其实都没什么,但有的文字离谱到诋毁我母亲的地步,如果不是谣言导致的误会,那就是心理太阴暗。上网发现有的诗篇非本人所作,也署名樊忠慰,并自翊妖精和盛装的姑娘,有意思,这是文友在开玩笑吗?盐津的吊钟岩并非魔教的黑木崖,我也并非当今的东方不败。虽偶尔胡言乱语,但没疯到阴阳颠倒的地步。这位高人,请勿妖言惑众。你送我的伪作我不稀罕,我连自己的诗都不稀罕。 陈:我读你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有这样的诗句:这无法游泳的海/只能以驼铃解渴/每一粒沙/都是渴死的水。你是怎样的心境写出这样的诗句?
樊:这是发表在1992年《诗歌报》9月号上的作品,已记不清写作的具体时间,我写东西写过便忘,也不太会谈创作感想。应该是在疾病与爱情的双重焦灼状态下,沙海这个幻象在情感和心灵镜片上的折射和流露吧。重庆诗评家马立鞭曾在1993年《写作》第一期撰文提及此诗,称此诗是惠洪《冷斋夜话》“诗者,妙观逸想之所寓也”的极好注脚,歌吟浩瀚戈壁的不少,从此角度切入绝无仅有。以此诗论,显然句句紧扣沙海无水这一人所共晓的常识做文章,所以幻化程度虽高,仍真切可感。第四届云南省文艺奖评委甚至有些夸张地写授奖辞,“每一粒沙,都是渴死的水”,仅此一句,便可以得奖。我从1991年夏生病至今已有十五年,十五年,几岁的孩子也变成了小伙和姑娘,这个患病的过程真像是沙海里跋涉,健康者无从理解这种痛苦,歧视、误解与偏见在所难免。我很理解那些因病而不幸自杀的诗人,海子、戈麦,徐迟,昌耀,他们的命运也许是人类终极命运的缩影,我理解他们,但我永远不会选择自杀。我是信奉宁为瓦全,不为玉碎的人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幻听,思维鸣响,时而抑郁时而狂躁的病症,令人在失控的状态下丢人出丑,即使伤痛到流泪淌血的地步,我也不忘自己坚定的暗示自己,要挺住,人完蛋了,一切都完了,一定要活出健康和诗歌,直到幻听的诅咒和嘲笑消失,至少要活到罪恶的幻听与我一起消失,想想未来,我也该有更重要的事,恋爱、结婚,让我的沙海淌出清泉和爱我的姑娘。时代像机器一样运转,有人发财,有人做官,有人落魄,有人升天。我在小峡谷被毒蛇般的病魔纠缠。这几句诗写得轻松,写诗的人活得不轻松。
陈:我感觉你很孤独,这种孤独来自外部环境,还是你个人?
樊:孤独的感觉不能写在纸上/写在纸上便不再孤单/莫说诗人清贫疾苦/大众的命运也相差不远。这是我新近写下的诗句,孤独并非我独有,每个个体者都是孤独的。我的孤独来自环境,也来自个人,根本在于疾病。没有人能代替我或者或者死去,没有人能代替我生病或吃药。灯红酒绿,喧嚣繁华的浮世并非真相。我一直在思索生命的本质和意义,及其这表象背后的根源,但不得而知。孤独感袭来,我就唱歌,阅读,踢球,或参加同事组织的郊游。一次登山鞋坏了,我在百货公司门口把旧鞋脱下,赤脚走进鞋店,那些人冲我发笑。我说,没鞋穿我才来这里呢,有什么好笑?我有时自然真实得有些滑稽。幻听的存在,让我听见了你们听不见的赞美或诅咒,思维鸣响的病症,会剥夺我思想的自由,让我迷惘而绝望。毫无疑问,它们若非来自我生病的大脑,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发病初,我难以适应,为摆脱其干扰控制,我多次外逃,险些饿死异乡。并被巡警拘禁和殴打。几乎同时,我在《诗刊》发表短诗五首,有人戏称,像范进中举一样,发了几首诗就高兴疯了,其实这是误解了。多年来,我一直服药,断续地上班,我不可能以一个健康者的心态和视觉去看待生活和世界。有时我又觉得我比药品还要健康。也许我一生最好去处是精神病院,但我对诗歌有幻想,对爱情有美梦,对未来有忧虑,这使我善良得愚蠢,幸福得忧伤,悲观得坚强。我其实是一个怀疑语言的人,却痴迷诗歌,真是矛盾。由于我天性疏懒,散淡,又不善交际,愈使我返照心灵的幻听的痛苦,让我像一只长尾巴的猴混入人群,自己不自在,也让别人不自在。如果说我与环境不协调,那也不过与诗歌在当今现实的尴尬处境相似,有些话我想说,说出来许会引发更多的误解,不如不说的好。我特别害怕好话,再多的夸奖也不能淡化或抵挡幻听对我的嘲笑、诋毁与谩骂,有时反而加重,不是我没心没肺,真是这样的感受和想法。有人以为我不知道自己诗作的价值,我觉得自己有几首小诗不错。病苦常使我万念俱灰,想世间事物,有时觉得,关于诗歌,伟大与不伟大也不过一句空话。生病多年,累及父母亲友,关心过我的人也不少。2001年在昆钢读书铺住院期间,黄尧、李仕良、欧阳常贵、潘灵、宋家宏、雷平阳、朱宵华、王宁等人也曾到医院探望,当我发病,被迫用意念与幻听对话或抗争,亲人或朋友,都要疏远,太亲近,不是亵渎,就是怠慢。这种感受在我的一些诗篇也有流露和表现。不管怎样,我都是常为自己骄傲的人,不为诗歌,只为我还活着。疾病和伤痛算什么,死去的是无从捉摸的时间和黑暗里影子般的孤独。
陈:你以后会坚持下去吗?在你看来,诗歌在你生命中占什么位置?
樊:未来的事,谁也说不准,但诗歌曾是我的救命稻草,倘若没有诗歌,仅仅靠药物,这十多年的病恐怕熬不过来。报上说,读诗可以治精神病,我这写诗,可谓从病的骨子里治病吧。记得少年时放学回家路上,看见一群人迁坟,用拾粪的竹叉把死者的骨头点点拣放进一个瓮里,我真切目睹了生命的本相,死亡的卑贱和丑陋,感到有些晦气和难言的害怕。不停地吐口水。那年代,我们早已习惯喊万岁这些口号,但永恒这个概念还不太能理解,知道文章乃经国大事、不朽盛事是后来的事。写诗就是用文字询问自己,我能抵达永恒吗?诗歌在我生命中相当重要,但肯定不是唯一,身边的朋友说我不像文人,我说自己不文不武,是个粗人。我写诗,大家看到了我的诗,其实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与病魔的搏斗和胡思乱想上,我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撑这个患病的身躯,有时不免癫狂。多年前,我在昆明的一家报纸上自我炒作。“我是精神病患者或先知,弱智或救世主,通灵诗人或白痴。”我曾经崇拜汉字,妄图用汉字让死者复活,当然,未能如愿,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耶稣。你问我这几个问题、我也就如实回答,不知是不是答非所问。不久前的省作代会,你给我代表证,那个编号我喜欢,是我多年来揣在心上的数字,你也许知道,如果不知道,读我的《精神病日记》就知道了。谢谢你对我的采访,请让我借《文学界》的宝贵地登一则征婚启事,
可以吗?亲爱的姑娘,如果有谣言,请不要相信,如果好奇,请不要喧哗,如果恐惧,请不要害怕。带上你花朵的容貌,冰雪的贞操,像爱上一个衰老的儿童,嫁给我吧!嫁给一个健康的疯子,一个智慧的先知,一个写诗的傻瓜。神在高处,要我说出这些话。